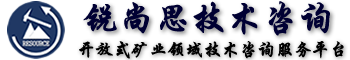陈 源
中外资源量和储量分类对比时,通常涉及两个层次的对比:规范层面的概念性对比和资源量/储量估算操作层面的结果对比。从逻辑角度看, 资源量和储量估算结果是最终表现形式,也是多数读者的关注点。
我国矿业行业常见规范层面的中外资源量和储量分类概念对比,通常脱离操作层面的内容,容易导致相应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同时,熟悉我国资源量估算操作层面的专家更容易强调我国资源量和储量估算的合理性,并由此产生若干歧义性争议。
事实上,西方的规范是市场洗礼后的一个暂时性的动态技术性规则,其思维逻辑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 并更多强调的是对原始数据的约束,并没有完全限定资源量和储量的估算方法和程序。原始数据包括原始数据的产生过程,主要指地质勘查和可行性研究过程,以及资源量/储量估算时,其资源量/储量估算人对原始数据的查证过程。资源量/储量估算过程和结果属解译性资料,其合格性要由其同行来判断。由此,我国资源量估算专家容易导致下列歧义性认识:
- 原始数据的客观性和合格性不是资源量和储量估算的核心内容。这一认识源于非市场条件下的事实假定。事实上,这个问题正是西方规范的核心内容,即勘查和可行性研究过程要有明确的合资格人对其负责,资源量/储量估算人员要交待如何对原始数据的合格性进行确认,是否可以用于资源量/储量估算。如果可以,则其结果由资源量储量估算人员负责。
- 地质统计学软件对资源量/储量估算结果通常是西方规范要求的结果。西方规范目前没有对资源量/储量估算方法进行限定,事实上地质统计学软件与西方技术规范要求没有直接对应关系。
- 资源量/储量估算结果应该是严肃的和权威性的。事实上,中外资源量估算专家对此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西方的资源量/储量估算结果的权威性与我们的理解是不同的。西方规范强调的是估算模型的客观性和合理性。针对资源量,其估算结果仅仅是其合资格人依据合资格人自身的资源开发概念性模型所确定的边界品位以上的资源量结果,给出该结果的同时还需要提供不同边界品位条件下的资源量估算结果。对投资方来说,则需要审视合资格人相关风险方面的描述来做自己对边界品位的取舍和判断。针对储量,其合资格人仅仅是对预可行性研究获得的储量估算结果的合理性验证,即同时需要提供预可行性研究的可开发利用资源量(储量)结果和合资格人的储量估算结果。对投资方来说,同样需要审视合资格人相关描述来做自己的取舍和判断。因此,西方的资源量/储量估算结果在形式上是严肃的,但不是关注点的全部,其权威性是不足的,强调允许同行对其估算结果进行监督和挑战。
- 资源量/储量估算结果应该是可对比的。这里的关注点是同一矿床资料在同一规范指导下不同合资格人的资源量/储量估算结果允许有多大差异?西方的规范并没有对估算方法、参数等进行约束,即允许不同的合资格人有相当的自主权。但是,西方规范对合资格人的估算结果是有约束的,主要约束有:合资格人要充分披露估算方法和参数,并给出估算过程中的新增误差评述意见,同时接受同行对其估算结果的监督。目前西方规范本身多数没有对不同合资格人估算结果之间的相对偏差进行明确规定,但整个行业要求不大于10%。可以看出,对资源量/储量估算结果的合理性进行评判时,除规范的明确约定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业的一般操作程序。
鉴于上述讨论,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 地质统计学软件对资源量/储量估算方法与西方技术规范要求没有直接对应关系。或者说,我国目前的资源量估算地质块断法和剖面法与西方规范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地质统计学方法的优势在于在资源量估算过程中能充分反映品位的局部变化,整体上来说一般不会新增误差。我国目前的估算方法实际上为经典统计学中的加权平均法,因为估算时所取赋值块断过大,品位的局部变化将在相当程度上发生均化。这个过程导致的新增误差也很难评估。所有,国内外业内均倾向采用地质统计学方法以及相应的软件。
- 基于同一资料和同一西方规范,不同的合资格人的估算结果是有差异的,有差异是一个合理的现象,但不同合资格人估算结果之间的相对偏差不能大于10%。这里的估算结果比较时不包括Inferred(333)资源量。在西方的规范里,Measured(331)和Indicated(332)资源量与Inferred(333)资源量之间存在质的差异。就Measured(331)和Indicated(332)资源量而言,中外资源量估算矿石量结果一般是可以对比的,但相应的平均品位是有差异的。平均品位的差异主要因不同的估算方法和操作层面上差异引起。
- 除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外,执行西方规范要求的资源量/储量估算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受行业一般操作程序约束,也可以理解为行业多数人的操作程序就是相当程度上的标准。需要明确的是,我国矿业界的相应规范对资源量估算操作层面有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的最大优势是不同资源量估算人员的估算结果的可对比性较强,即使Inferred(333)资源量,其在我国的可对比性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中外资源量和储量分类对比时涉及的资源量和储量估算结果对比更多的表现是中外矿业行业的一般操作层面上的差异。这一差异可分为两类:西方的地质统计学与我国的地质块断法和剖面法之间的差异,以及西方的地质统计学应用与我国的地质统计学应用之间的差异。前者实际上就是地质统计学与经典统计学之间的差异。所谓我国地质统计学应用目前多数是将地质统计学方法修正,并应用到我国现行资源量估算的操作层面上,由此产生中外资源量估算系统性差异,其结果通常是:我国的331+332矿石资源量偏低、平均品位偏高,333矿石资源量普遍偏低。
通常情况下, 中外资源量级别划分概念上大致是一样的,即331工程网度对应Measured资源量,332工程网度对应Indicated资源量,尽管西方多直接采纳可信度距离来划分资源量级别。然而,我国相应技术规范规定332工程网度以外无论是否有333工程,一律视为333资源量,即332工程网度以外不得“外推”。西方认为,一个矿床Indicated资源量大致对应的工程网度以外务必在部分矿段要有Inferred资源量对应的工程网度,以证明Indicated和Inferred资源量级别划分的合理性。在此前提下,Indicated资源量大致对应的工程网度与外围Inferred资源量对应的工程之间矿化域是有采样工程的,因此,Indicated资源量大致对应的工程网度与外围Inferred资源量对应的工程之间有一部分资源量被视为Indicated资源量的可信度范围,不涉及“外推”问题,而这部分资源量在我国因为规范约定而划分为333资源量了。当Indicated资源量大致对应的工程网度外围没有控制Inferred资源量的工程时,依据控矿因素,一样可以有部分可信的Indicated资源量和可信度较低的Inferred资源量。另外,我国技术规范对矿化体的无限外推作了明确规定,而西方规范认为,矿化域(矿化体)如何外推应该由合资格人说了算,只要合资格人能说明其外推程序的合理性即可。因为上述技术规范上的差异,西方Measured +Indicated矿石资源量要略大于我国的331+332,而Inferred矿石资源量则普遍大于我国的333资源量。
在我国,将矿化体范围替代矿化域概念后的直接结果是导致赋值前的源数据集结构发生变化,即人为提高源数据集的平均品位,对应的特高品位也会相应提高,赋值后的平均品位在同等条件下也相应会提高。西方在资源量估算阶段,一般不涉及“夹石”问题,因为是否判定为夹石应该在储量转换过程中由采矿工程师判断并确定。在确定矿化域范围的时候剔出“夹石”的后果是再一次人为改变源数据集结构。我国在资源量估算阶段,将资源量和储量的概念混合在一起,即在确定矿化域时就考虑确定未来的可开采矿体,直接确定未来的可开采的矿体边界,并剔除不易被开采的夹石是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可以说,西方同行对我国资源量和储量估算过程中的操作方式是有异议的。
可以看出,中外资源量和储量分类对比在规范层面上的概念性差异不大,但在资源量估算操作层面有操作方式上的较大差异,其结果存在系统性相对偏差。对储量来说,中外在概念和操作层面差异性较大,目前不存在可对比性。